炎炎夏夜,酷热难耐,尽管有冷气降温,但仍是心神不宁,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好。在经过一番坐卧的纠结之后,无奈的我选择了音乐,在消磨时光的同时,为“发热”的灵魂找到防暑降温的甘露。
流淌的音乐行云流水、余音袅袅,让我孤独且躁动的情绪逐渐安静、温润,进而开始全神贯注,用心倾听,享受着音乐的圆润与柔美。
蓦然间,伴随一段陌生的旋律之后,传来的却是熟悉的声音,走近屏幕一看,原来是降央卓玛在演唱《心灵睡过的地方》。孩子要找妈妈老人手指远方那里是无边的青草香是我的心灵睡过的地方睡过的地方游子归来了泪水湿了衣裳河水洗尽红尘忧伤抬头望一望阳光万丈我的童年刹那回到胸膛
 (资料图)
(资料图)
伴随着优美的马头琴声,天下最美女中音的歌声,瞬间把我自高楼大厦的省城带到桐柏山南麓那低矮的土坯房中。那里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我躯体睡觉和灵魂栖息的地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溪一塘,童年的一轶一糗、一幕一桩,都萦绕在眼前。
在鄂豫交界、丘陵与高山转换的广水市北部小镇旁边,有一片因山水冲击形成的小小“平原”,面积约五平方公里左右,散落着四个自然村,加几家独门小院,大约有六、七十户人家,五百人。一条记忆中只干涸过一次的小河,成弧形环绕着从小“平原”的边缘缓缓流向远方,那可是我们近五百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了两座水库,更是让这片土地旱涝保收,物产渐丰。
在平原的中部偏山边,有一个叫大土城塆的自然村,住着近30户人家,绝大多数为程姓,其他姓氏也就六、七家,就连我这天下第一的姓氏,在当地也是小姓,才两户。
村子的四面有三面有水塘环抱,加上远些的小河,或者是临村灌溉用的沟渠,还真有四面环水的感觉。
村子不大,但四面都住了人家。
在西边,两间狭窄与三间更加狭窄的土坯房,与邻居家的院落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出生在这低矮、狭窄的空间里。
我记事的时候,尽管大哥、二哥已经从军去了,但八口长住肯定让房间十分拥挤。我和尚未成年的哥哥睡通铺,姐姐、妹妹住一起,其他的为父母的房间、客厅、厨房。还有存放农具、鸡鸭过夜的角落。虽然紧凑,但却有序。只是下雨时,经常是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屋外不下,屋里照样下。尤其是小小的院落,遇到暴雨,雨水就排不出去,变成小小的池塘,似乎还有一次在院子里都抓到鱼了。
院子里有一株茂盛的栀子树,花季到来的时候,清香满堂,让人心旷神怡。母亲和姐姐会经常摘来送人,就连我这男儿身也会经常摘几朵放在书包中或者是课桌的抽屉里。大门右边约十米左右的地方,有我家的两棵香椿树,一棵泡桐树。春季到来,万物复苏,那鲜嫩的香椿芽便被父母或者兄姐弄下来换盐、换醋、换酱,偶尔也会成为我们碗中的美味。
村南的学校,建在一个小山顶山,是村办小学,设有一到五年级五个班,学生不到百人。后来在我们毕业后,还戴帽办了初中,增加了两个班,早我一年毕业的兄长成了初中班的老师。
说起学校,还有一段三迁的故事,一、二年级(一年级读了个复数)是在我新建的房子后面的小土城里读的,离我家大约三百米。
后来因学生人数增加,原来的教室容纳不下,就在村南头修建新的学校,只是时间太紧,没有建设好,便在更南边的另一自然村借仓库过渡,那距离稍远,超过了千米。
经历了大半个学期之后,才搬到新的学校。小学毕业后就到镇上去读初、高中,但距离也近,离学校近成为我读书的先天优势。
那灌溉的沟渠,潺潺的小河,不仅是伙伴们嬉戏、水战的乐园,更是抓鱼摸虾的战场,尤其是插秧时节,或者是夏日的雷雨之后,我都能凭借双手,给全家带来惊喜、带来佳肴。多少次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田间、水沟里的鱼儿,我都以饿虎扑食般的迅速将其收入囊中,给家里改善伙食创造条件。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那就是身上带有保护液体的鲢鱼,过于光滑,如果不能一击中的,就会让其从手中逃走。
分布在村子三面的塘堰,那满塘的碧水,不仅是我们自学游泳的“训练场”,更是洗净一天疲劳和汗水的天然澡塘。
少年的我们随时都能跳进塘里游泳、嬉戏、水战,年长的男性则要等到天完全黑了才会去洗澡,自然是要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那弧形环绕在“平原”边缘的小河,一旦秋天临近,枯水期到来之前,村里就会在河上筑起临时水坝,装上水车,搭上草棚,开始为全村人轧棉花,为村民们解决棉衣、棉裤做准备,为冬天的纺织准备原料,为来年的春夏创造条件。透过那简陋的设备和工艺,让我们体会到了前辈人的勤劳和智慧,让自耕自足的农业社会延续了几千年。
河的西岸,是村里分给村民的菜园(自留地),种植的蔬菜,除了满足家人生活的需要,还会拿到集市上去换钱,然后换回日常生活的必须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小河被称之为园子河。其实,不管是谁家,都会尽可能从家人的牙缝中抠出一些蔬菜,拿到集市去换钱。只是年少的我们,尽管知道家庭生活的艰辛,但也会经常光顾菜地,“偷食”菜地里的果蔬。但“偷食”严格遵循着“楚河汉界”的界限,自己“偷食”自家的果蔬,绝对不会越界。
那离村子数里的群山,是我们烧柴的产地。每到夏天,那低矮的荆棘枝,易于枯荣的茅草,都成为我们“争夺”的对象,砍下了,都得挑到村子附近才敢晾晒,因为在深山中容易被别人“抢收”。为了让生米能成熟饭,我们也曾“抢收”过别人晒在深山的成果,有时候还会违法地去干一些偷盗之事,那就是到其他生产队的地盘上去砍自己能扛得起来的松树,回家当劈柴烧。
清明到谷雨之间,我还会同小伙伴们利用课余时间,一起上山在乱石堆去掏蜈蚣。
那可是一件危险且刺激的游戏,若不小心被蜈蚣带毒的钳子钳了,便疼痛难忍,到第二天鸡叫时才能缓解好转。
如果运气差了,蜈蚣没有掏出来,先掏出蛇来,会让人一整天都情绪低落,因为蛇同“赊”同音,有了蛇就掏不到蜈蚣了,如是,前辈们让我们把那冷血动物称为“钱圈”,为的是图个吉利。
秋天的时候,我们还会结伴上山采木子、油桐,送到供销社去变现,尽可能地自己解决自己的书本费。
那祖辈们留给我们的有限土地,更是我们“结两手老茧,炼一颗红心”的阵地。“双抢”时节,我们这群少男少女便成为抢收、抢插的主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疲劳不疲劳,你都得想方设法在指定的时间完成“双抢”任务。好在,“双抢”的时节,我每天都能挣到全劳力才能得到的工分,可以为减轻母亲的些许负担,为自己的温饱多挣些筹码。
那离村不过千米的集市,更是我们逍遥、娱乐的胜地,农闲、课余的时间,我们便会三、五成群地赶集去。
说是赶集,其实是无所事事,别说家徒四壁,就算家里有钱也轮不上我们上街采购。如是,我们便穿梭在供销社各个门市部之间,当然还是新华书店要多一些。只是那时的书店不同今日,是封闭式管理,去了也只能一本本的让营业员递给你,然后装模作样地翻看一番,时间不能过长,否则让营业员发现你是在混免费的书看,会立即索要回去。偶尔也会同其他村的孩子们斗嘴,合适的时候还会抖抖威风,约个“决斗”什么的,但经常是不了了之,没有谁会真正记得“决斗”的日子。
小路上,我们推过铁环,也割过猪草,抓过蜻蜓。操场(打谷场)上,我们弹过珠子,抽过陀螺,拍过烟盒,跳过绳,踢过毽子,跳过房子,还打过弹壳。
房前屋后,我们爬墙上树,掏过鸟窝,套过知了,用弹弓打小鸟,用水枪喷伙伴,猜过东西南北,躲过猫,下雪的时候还打过雪仗、“滑”过雪、“溜”过冰。
安静的手机突然传响起另一首乐曲,把我从遐思中惊醒,原来是“老板查岗”的时间到了。我关掉音乐,收回了思绪,朝着故乡的方向眺望。那贫穷落后的乡村,尽管今天也不富裕,但毕竟养育了我们,让我们永远的依恋和铭记。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牵挂、思念,希望有哪么一天能重返故里,任凭思念的脚步,去寻觅那逝去的足迹。
(来源:一个人的宅)
 小狗误食6粒布洛芬器官衰竭死亡!这4种人群建议吃乙酰氨基酚! 【存放好药物! 小狗误食6粒布洛芬器官衰竭死亡 ,医生:药物吸收过多致多器官衰竭】
小狗误食6粒布洛芬器官衰竭死亡!这4种人群建议吃乙酰氨基酚! 【存放好药物! 小狗误食6粒布洛芬器官衰竭死亡 ,医生:药物吸收过多致多器官衰竭】
 春节快递有保障了!这些快递公司承诺部分地区春节不打烊 12月20日国家邮政局印发《关于切实畅通邮政快递服务保障民生物资医疗物资寄递的通知》
春节快递有保障了!这些快递公司承诺部分地区春节不打烊 12月20日国家邮政局印发《关于切实畅通邮政快递服务保障民生物资医疗物资寄递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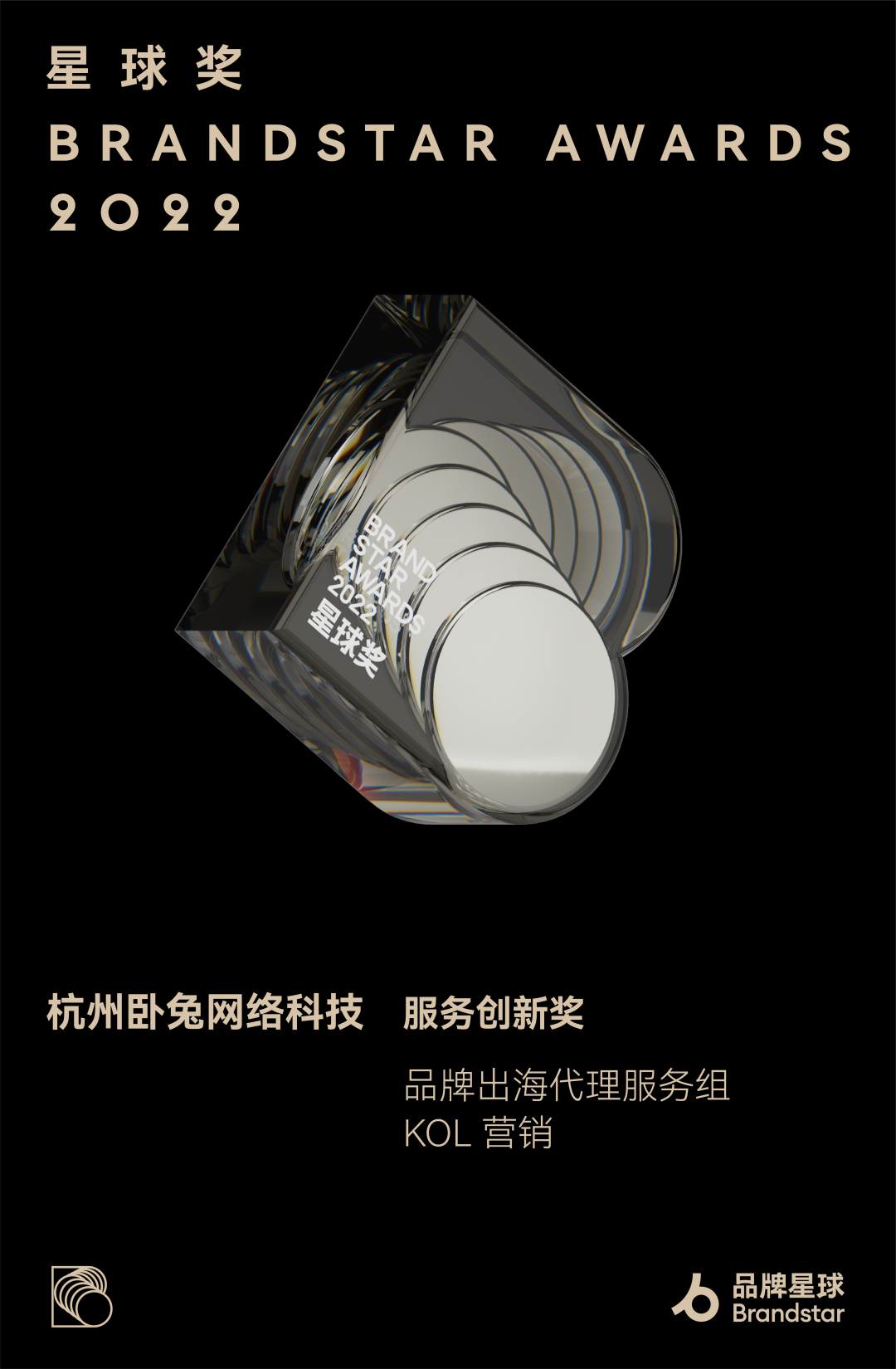 荣耀加冕 大道可期 | WotoKOL卧兔荣获星球奖BrandStar Awards 2022服务创新奖! 2022年11月,星球奖BrandStar Awards 2022获奖名单揭晓,WotoKOL卧兔荣获服务创新奖
荣耀加冕 大道可期 | WotoKOL卧兔荣获星球奖BrandStar Awards 2022服务创新奖! 2022年11月,星球奖BrandStar Awards 2022获奖名单揭晓,WotoKOL卧兔荣获服务创新奖  科治好:坚持坐高电位,绿色安全,让身体回到舒适的状态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由药物治疗向非药物治疗的观念转变,也是许多人的共识。相较于药
科治好:坚持坐高电位,绿色安全,让身体回到舒适的状态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由药物治疗向非药物治疗的观念转变,也是许多人的共识。相较于药  科学指南针8周年视频燃爆科研圈,它是如何引发科研人共鸣的? 科学指南针8周年,为更好做科研,12月22日,在科学指南针官方微信视频号中,一段近三
科学指南针8周年视频燃爆科研圈,它是如何引发科研人共鸣的? 科学指南针8周年,为更好做科研,12月22日,在科学指南针官方微信视频号中,一段近三  唯蜜瘦便携式腹部智能按摩仪入选工信部2022年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例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2年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入库案例名单,全国共
唯蜜瘦便携式腹部智能按摩仪入选工信部2022年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例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2年移动物联网应用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入库案例名单,全国共  一招短线选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盘买入法的好处有哪些?拉尾盘什么意思? 尾盘买入法:属于短线的操作,今天买了,明天就有机会卖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时候有
一招短线选股法是什么意思?尾盘买入法的好处有哪些?拉尾盘什么意思? 尾盘买入法:属于短线的操作,今天买了,明天就有机会卖的。每天下午14:30分的时候有